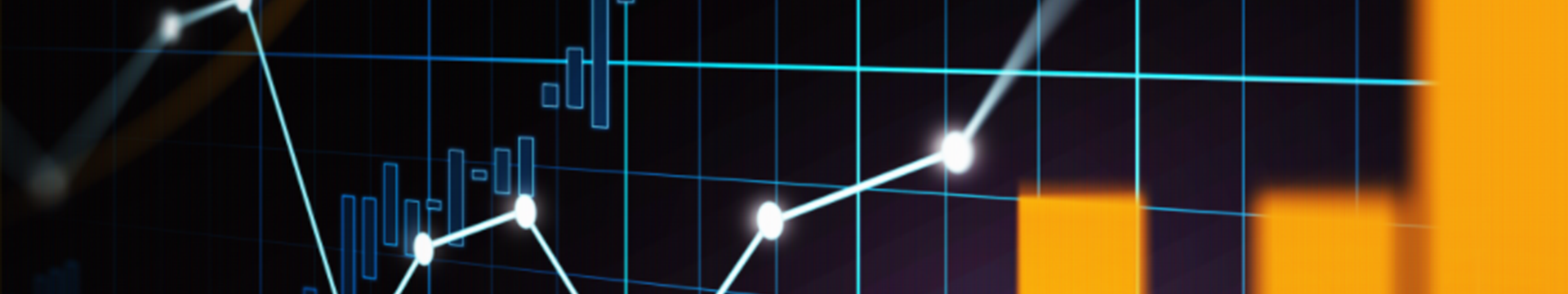导读:本文模型基于一个两部门的新凯恩斯模型,即包括绿色和非绿色部门。当面临正向绿色技术冲击时,受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情形会使得利率下降的更少,使得常规货币政策难以有效的抑制(负向)通胀缺口,使得产出上升得更少。
一、研究背景
气候变化已从边缘问题转变为全球性议题,并成为学术界、工业界和非专业人士都在关注的热门话题。因此,越来越多学术研究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温室气体 (ghg) 减排战略已成为一项优先的国际议题。自1992年里约会议以来,学术界和政界就增长与环境治理的权衡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讨论的重点是经济活动如何与环境问题保持协调(“可持续增长”),而不是被假定的相互互斥性所阻碍。然而实践中,尤其是在中短期,既要维持金融和经济正常活动,又有实施环境政策的紧迫性,这迫切需要可持续的(短期)经济政策,能兼顾环境质量和经济效率以及解决金融稳定问题。考虑到温室气体减排的潜在高附加成本,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可能会严重影响宏观经济活动(转型风险),这尤其令人担忧。随着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对整体经济的重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宏观经济学和宏观金融等领域的研究正在解决这些问题。
二、模型设定
本文模型基于一个两部门的新凯恩斯模型,即包括绿色和非绿色部门。代表性家庭部门可同时向两部门提供劳动力,并且可以选择把前借给政府或者金融中介。每个代表性家庭都有银行家和工人,但家庭不能把钱借给家庭内成员拥有的金融中介。银行家和工人可以互相转换,每期都有一定比例的银行家以一定概率“存活”到下一期,剩下的会转变为工人。存活的银行家把其留存收益支付给家庭用于设立新的银行(金融中介)。家庭同时面临时间偏好冲击。
企业部门最终产品部门的投入品包括绿色部门和非绿色部门中间品,其生产技术是ces型生产函数。而绿色和非绿色部门各自都包括无穷多个企业的连续统,两部门内部各自都为垄断竞争市场。中间品部门为柯布-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投入要素包括资本品和劳动。产出面临污染负外部性,环境污染对生产函数的损害为二次型函数。绿色和非绿色部门都会产生污染,企业会花费一定成本进行减排。两部门企业各自面临calvo粘性价格设定。
本文假定家庭部门拥有资本品生产部门,资本品部门向绿色和非绿色部门出售资本品,资本品的生产面临调整成本。金融中介可投资于两部门的企业,并受到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约束,即满足资本充足率(金融中介净资产不低于加权风险资产的一个比例)约束。
中央银行常规货币政策遵循带利率平滑的泰勒规则,并且可以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如企业债购买计划(cspp)来代替金融中介向企业提供融资。宏观审慎政策规则遵循巴塞尔协议iii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政府向企业与金融机构征收碳税,并为财政支出(占gdp比例固定)融资。
三、模型主要结论
首先,本文对比有无零利率下限时的经济动态对比。当面临正向绿色技术冲击时,受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情形会使得利率下降的更少,使得常规货币政策难以有效的抑制(负向)通胀缺口,使得产出上升得更少。而基准模型相比受零利率下限约束的情形,绿色产出会上升的更多,非绿色产出下降的更多。在负向偏好冲击中,总产出和总排放在基准模型中上升得更多,而消费与利率下降得更多。零利率下限会使得经济复苏的速度更慢并使得排放下降得更多。
然后本文对比了有无气候政策下的经济动态,气候政策为《巴黎协定》将排放削减20%的目标。在基准模型中,绿色技术冲击会提高绿色产出,总产出也上升。同时,总排放因为非绿色部门的产出下降而下降。绿色或非绿色技术冲击都能使得家庭消费水平提高从而财富增加。当引入环境政策(环境税)时,绿色技术冲击下绿色部门的产出会相比无政策有所下降,因此绿色部门的排放也会下降。而对非绿色部门而言,环境政策则使得排放下降得更多,因此总排放水平下降更多。但面临非绿色的技术冲击时,总排放量的结果会与绿色技术冲击相反,显示了环境税制度存在一定的顺周期性,所以最优的环境税率也应当在繁荣期提高,在萧条期下降。负向偏好冲击会有相似结果。
再次,本文研究了最优的环境(财政性)政策。但本文发现最优的环境税水平很小(0.3%左右),这意味着就家庭福利而言,环境税对家庭消费水平影响更大,而气候变化通过影响产出水平而对家庭福利的间接影响则很小。因此,环境税试图解决的由温室气体外部性引起的经济低效率仍然无法仅通过引入税收政策来解决。因此,宏观审慎和货币政策可以在缩小低效率差距和帮助实现缓解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通过多个方式来试图实现宏观审慎政策。第一种方式仿效gertler(2012)方式向金融机构征税补贴外部股权。第二种方式是差别化的绿色宏观审慎政策。为此,政府通过对非绿色资产征税来补贴绿色资产和外部股权,保持银行家的资产负债表不变。gertler(2012)方式的宏观审慎政策能更有效地减少冲击对信用利差的影响,但绿色宏观审慎政策对非绿色部门信用利差的影响更大,而对绿色部门信用利差反而几乎不起额外作用,这可能是因为银行转向污染部门时,资本充足率指标更好,从而对市场价格更不敏感。并且,从福利的角度来看,将碳税与绿色宏观审慎政策搭配起来效率更高,因为它比仅依靠税收政策实现相同程度的排放,产出减少的程度更小。
通过进一步研究量化宽松政策,本文发现量化宽松更适合抵消排放冲击对风险溢价的影响。因此可以实施随时间变化的差别化宏观审慎政策来促进绿色部门的中期增长(从而降低单位排放强度,同时对福利的影响最小),同时量化宽松政策可用于抵消因排放冲击引起的短期利差变化,从而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效果。通过研究实施资产购买计划,绿色非绿色部门量化宽松都会导致通胀率上升。而引入差别化的宏观审慎政策时,对通胀的影响略有减弱。这些表明绿色量化宽松也可以在低通胀预期的基础上实施。并且,引入碳税对量化宽松的影响具有积极的环境影响。因此,资产购买(量化宽松)应该被用作短期的逆周期调节工具,而差异化的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发挥结构性的作用。
四、政策启示
第一,在本文的分析框架种,在最大化产出和消费与减少气候变化的冲击之间存在权衡。特别是,我们发现需要征收10% 的环境税率以便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保持一致。然而,这些税收和减排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减排效率(即低转型成本),并且最优环境政策下环境税水平很低。这意味由于中短期税收对福利的影响是扭曲的,因此仅靠财政政策来发挥环境治理效果是不够的。
第二,由于环境外部性会影响风险溢价,并可能改变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短期逆周期调节政策工具非常重要,应在未来的气候变化减缓政策中使用。从货币和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发挥的作用来看,本文发现有利于绿色部门的贷款的差别化宏观审慎政策会促进绿色部门投资和产出,这意味着较低的排放产出比和最低的福利成本。
第三,对于量化宽松政策,本文发现碳税提高了绿色和非绿色资产购买的收益。然而,需要宏观审慎政策来激励中央银行进行绿色量化宽松。在绿色和非绿色量化宽松之间进行选择,意味着需要在更高的产出和更低的排放之间进行权衡。如果绿色部门的规模增长到与非绿色部门一样大或超过绿色部门,这种权衡就会消失。关于环境外部性的影响,本文发现量化宽松比宏观审慎政策在缩小无效率的风险利差方面更有效。另一方面,绿色宏观审慎政策更适合支持向清洁技术的转型,因为它不会显著地扭曲福利。